目录
快速导航-
华语作家访谈录 | 人民的立场就是作家的分寸
华语作家访谈录 | 人民的立场就是作家的分寸
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存在价值 舒晋瑜: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,初学写作,您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? 张平:山西的当代作家,特别是50后60后的作家,受赵树理、马烽、西戎、孙谦、束为、胡正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比较大,这些老作家也就是后来一直被中国文坛认可和称誉的“山药蛋”派作家群。这些作家曾在某一段时期内占据主流地位,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。我们几乎就是读着他们的作品成长起来的,他
-

气象 | 宰 牲
气象 | 宰 牲
-
气象 | 历史、现实性与力量
气象 | 历史、现实性与力量
一 自2000年伊始,直至2019年岁末,我个人写作生涯的一次长途跋涉终于结束了。 二十年,对于一生不算短了,对于一部长篇小说而言似乎刚刚好。 我曾在一些文学场合多次提及自己的幼年经历。那得从1976年初秋的一个早晨说起,那时我父亲尚在人民公社任会计,凭借算盘珠子和一支英雄牌钢笔谋生,他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,算盘更是打得像当下的年轻人敲击键盘那样飞快,他为人机敏严谨,不苟言笑,对我们兄弟几人
-
锐小说 | 岁月飘过塘子寨
锐小说 | 岁月飘过塘子寨
一 石匠伍是一个泥水匠出身的土匪头子。他的枪法准得吓人,百米外能打中电线头。他砌的石墙,在勐傣坝无人能及。 很多年前的一个秋天,太阳毒花花地照射着塘子寨。石匠伍用沾满稀泥的右手,狠狠扯了一把下身的大花裤衩。失去弹性的裤衩头,羞答答地贴服在他腰间。 “妈的,”他自言自语,“一个塘子寨乌鸦叫,不活人了。” “石匠伍,石墙不是用嘴巴砌的。乌鸦叫关你屁事,赶快砌石墙,要不然工时费就没了。”李圈官靠
-
锐小说 | 蝴蝶与战争
锐小说 | 蝴蝶与战争
上篇 一 妮从桌箱找出剪刀,把灯芯顶端的黑色部分剪掉,油灯亮度瞬间增加两倍。她抬头看哥哥,发现哥哥也在看着她,不禁莞尔一笑。哥哥也微微笑,低下头继续写。 为了躲避战争,我祖父带着四户人家共二十八人外逃,白天隐藏,晚上赶路,花了将近一个月来到这里。路边有一股清泉从石缝淌出,口渴的祖父接一捧水喝几口,喘着气说,又清又甜。他身后的人争先恐后地跑去接水喝,都一脸兴奋。我祖父笑着看他们一眼,转过眼去看
-
锐小说 | 说谎者
锐小说 | 说谎者
十分钟前,我被蒙上眼睛带到了这里。我记得先是上了一辆车,大约走了半个小时路程,下车,上石级,之字形的,再上木梯。我感觉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,风吹过来的力度大了点儿。脚下是木地板,不太光滑那种,地板上有少许沙子,踩上去会发出细微的吱吱响。我被带到一个椅子前,坐下。我在慢慢地适应这里,适应黑暗里肢体的协调性。带我来的人咚咚咚地下了木梯,很快我就听不见他的任何声息。我一时不知所措,双手一会儿放在膝盖上,
-
锐小说 | 痛 癍
锐小说 | 痛 癍
一 冷珊吃掉了一只苍蝇。 大苍蝇漂浮在白色的肥头鱼汤上面,身上沾满了白色发硬的液体,一看就是从苍蝇肚子里流出来的。身体卷成一团,蜷起的脚被一根发丝紧紧缠住。这俨然成了一锅毒药。客人一惊一颤像中了毒,要求饭店立刻写下承诺,承担因苍蝇引起身体任何不适的责任。包厢服务员冷珊似一个犯罪嫌疑人,众目似探照灯一般仿佛要把她融化。她哪里见过这个场面,她不知道要怎么应对,站在那里心跳加速却是面无表情一声不吭,
-
突围 | 走亲戚
突围 | 走亲戚
我们忽视了昂贵的高丽参,漠视了整齐排列的柏树,在洼地中,我们发现了盛开着的一朵朵蓝色的风信子,它们代表着新婚,根系横贯彭塔内拉山和艾岗山,是由当地的一位猎户移植过来的。猎人扎拉丰住在塔楼里,是个很有情调的男人,长相英俊但牙齿毛糙,他羞于绝望,但从不沉溺,他对挫折抱有一份腼腆的忍耐,他不过分审视命运,对他人的命途亦漠不关心。他认为,挫折降临,便是困难对他犯淫了,贫穷宠坏了他,它欲与他成为一体。他独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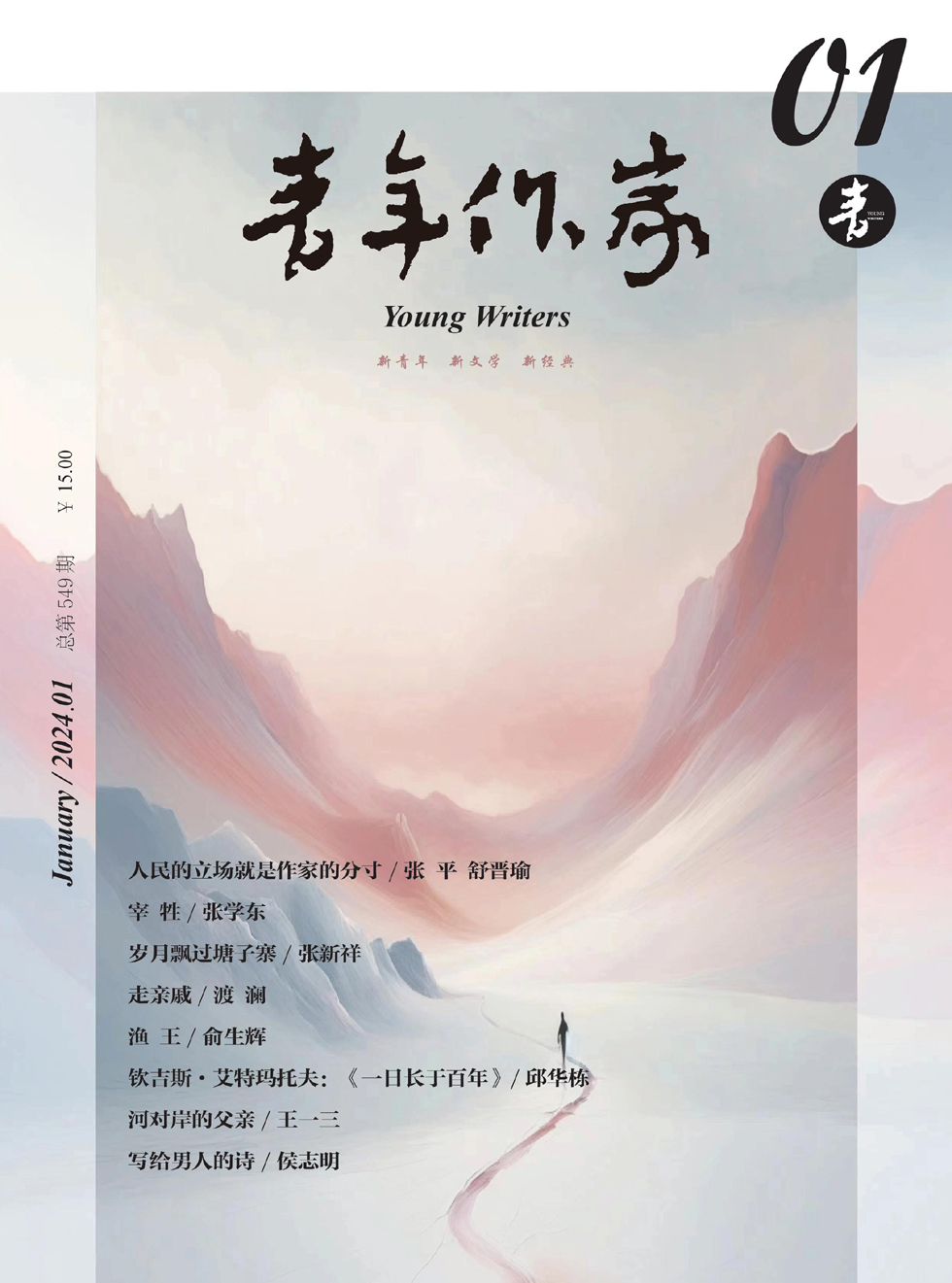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