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| 我希望
| 我希望
-
| 鸟迹【外一篇】
| 鸟迹【外一篇】
-
| 溯源牛河梁
| 溯源牛河梁
-
| 大山的深处
| 大山的深处
-
| 并不可靠的叙事
| 并不可靠的叙事
-
生活志 | 扎查梅朵:述与梦
生活志 | 扎查梅朵:述与梦
-
生活志 | 流动的家
生活志 | 流动的家
-
生活志 | 空心菜【外一篇】
生活志 | 空心菜【外一篇】
-
看·听·读 | 火焰中的暗影
看·听·读 | 火焰中的暗影
-
解释与重建 | 柚果落地
解释与重建 | 柚果落地
-
解释与重建 | 一间古屋
解释与重建 | 一间古屋
-
百花·自然书写 | 河流的封底
百花·自然书写 | 河流的封底
-
闲话 | 黄杨树
闲话 | 黄杨树
-
闲话 | 鸟遇
闲话 | 鸟遇
-
行旅 | 衔草寺幽魂
行旅 | 衔草寺幽魂
-
行旅 | 土地温柔
行旅 | 土地温柔
-
专栏 | 否定即强调,留白即覆盖
专栏 | 否定即强调,留白即覆盖
-
专栏 | 美的阅读理解与做题思路
专栏 | 美的阅读理解与做题思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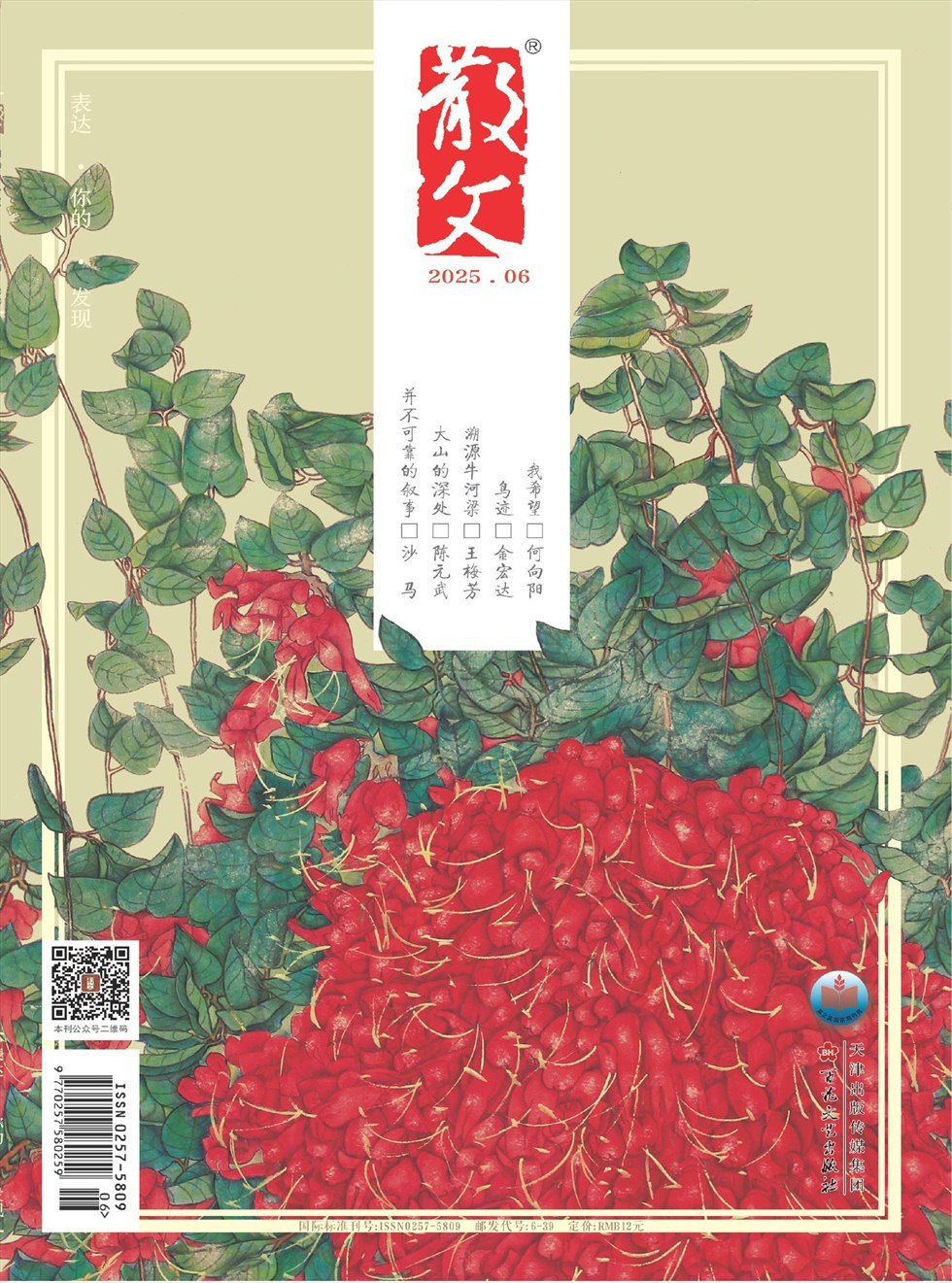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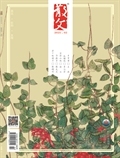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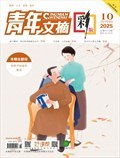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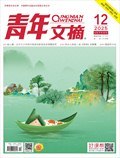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