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特别推荐 | 傅山的江湖
特别推荐 | 傅山的江湖
一战成名 长刀。枯叶。倦鸟。秋风。 崇祯九年(1636),一个傍晚,远天一片酡红,残阳如火如血。 随着吱呀呀的响声,一辆囚车朝京城的南西门缓缓而行。笼中囚犯正值壮年,披枷戴锁,衣衫褴褛,一路风尘,形容极显憔悴,只是双眉下的目光依然炯炯有神。 囚车后紧跟两位学子,年届而立,风华正茂。他们头戴儒巾,身着襕衫,肩上斜挎一个布包,却难掩贵气风流。进入城门,囚车停下,囚犯艰难地直起上身,一抖锁链,扭
-
特别推荐 | 燃灯者
特别推荐 | 燃灯者
一 夜已深。我在古老的书堆里已经穿行了很久,有些累了。突然看到一句话,仿佛一束闪电,照亮了整个世界。我一下子坐了起来。那是朱熹对孔子的一句评语: 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。 在朱熹的心里,孔子犹如太阳一样,照亮了黑夜。那时古人是相信天的,人是天地生的。所以说,上天若不生下孔子,整个人类犹如仍然在黑夜里行走,毫无目的,毫无方向。小时候,我有数次迷途的经历,记忆犹新。 一次是夜晚去看电影,三四个
-

特约专栏 | 灯穿影去
特约专栏 | 灯穿影去
-
作家视野 | 两地书
作家视野 | 两地书
阳明先生: 当我写下此笔的时候,我们已相隔整整四百九十五年了。 先生当然不可能知道我。这么漫长的时间,足以让很多的事情发生又消失掉了。死亡是经常性的,最关键的是,死亡之后的遗忘,更让人绝望,那遗忘充满了否定性。虽然,绝大多数的事物最终都将成为沙砾或野地里的狗尾巴草,但先生是极少数可以在肉身已去的情况下做到思想不灭的。 很多人拜于先生的门下。他们好像不只是为了求得学问,而是求学的路上,往往要走
-
作家视野 | 深夜长谈
作家视野 | 深夜长谈
那是一只模糊且清晰、旋转而静止、喧嚣又喑哑的泥碗。 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它的身上。无数个庸常的夜晚,一只泥碗的出现,让我和羽先生不再颓废,不再沉湎于后知后觉。黑夜和昏黄路灯的笼罩里,身体和衣襟以彻底敞开的姿势,对着白天、人群、黑夜以及暗中的事物说出所有被遮蔽与被隐匿的心事。黑夜以及黑夜裹挟而来的层层叠叠的暗物质,覆盖在我们身上,却没有丝毫沉重感、绝望感和幻灭感,相反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,不用再穿着
-
作家视野 | 暮色明亮
作家视野 | 暮色明亮
一 闹钟再次响起时,我睡得正酣,像一条鱼畅游在水里。仿佛水闸轰然巨响,水突然被抽掉,啪的一声,鱼摔落湖底。我无比懊恼,摸到手机将闹钟按掉,试图再寻找那片水域,却再也进不去了。不知从哪天起,每天早晨短暂的回笼觉,成了我每日赖以活命的水源。但水源紧缺,脑子依然一片混沌。 起身,去阳台待上一会儿。这十平方米的空间,是我私有的旷野,在每个晨昏接纳与安顿我沉重的肉身。为了让阳台更接近旷野气质,我热情又盲
-
作家视野 | 此岸
作家视野 | 此岸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布尔津县城里有两排最老的大树,它们是普通的杨树,不是那种笔直的穿天杨,就是散漫模样的粗大杨树,叶片比巴掌大,盛夏时节绿到几乎黑亮,生长在哈萨克小学校园的正中间,简直就是长长的苍绿蓊郁的拱廊,从正北的大门一直到正南的后门,一列有二三十棵,总共五十棵,一个怀抱那么粗。 还有一棵很老的大树,在南大桥进到县城的那截坡底下,守住了一个路口。这是一个大拐弯,旁边是哈萨克小学的土坯围墙转角,
-
别具只眼 | 喀什的时间
别具只眼 | 喀什的时间
时间是一万吨黄金,我只有一枚镍币 晚上十一点半,在喀什老街,还有小孩子在追逐打闹。我想拦住他们,撵他们回家写作业。明天不上课吗?孩子们奇怪地看着我,一溜烟儿跑到巷子深处去了。巷子掩映在铁线莲与鹅绒藤的绿叶中,这是本地特有的垂挂生长的绿植,在暖黄色灯光的映照下,巷子亦真亦幻,让人疑心这些孩子是不是阿拉丁,踏上了寻找神灯的历程? 这里是东五时区,而我来自东八时区,现在是上海晚上八点多的样子。不过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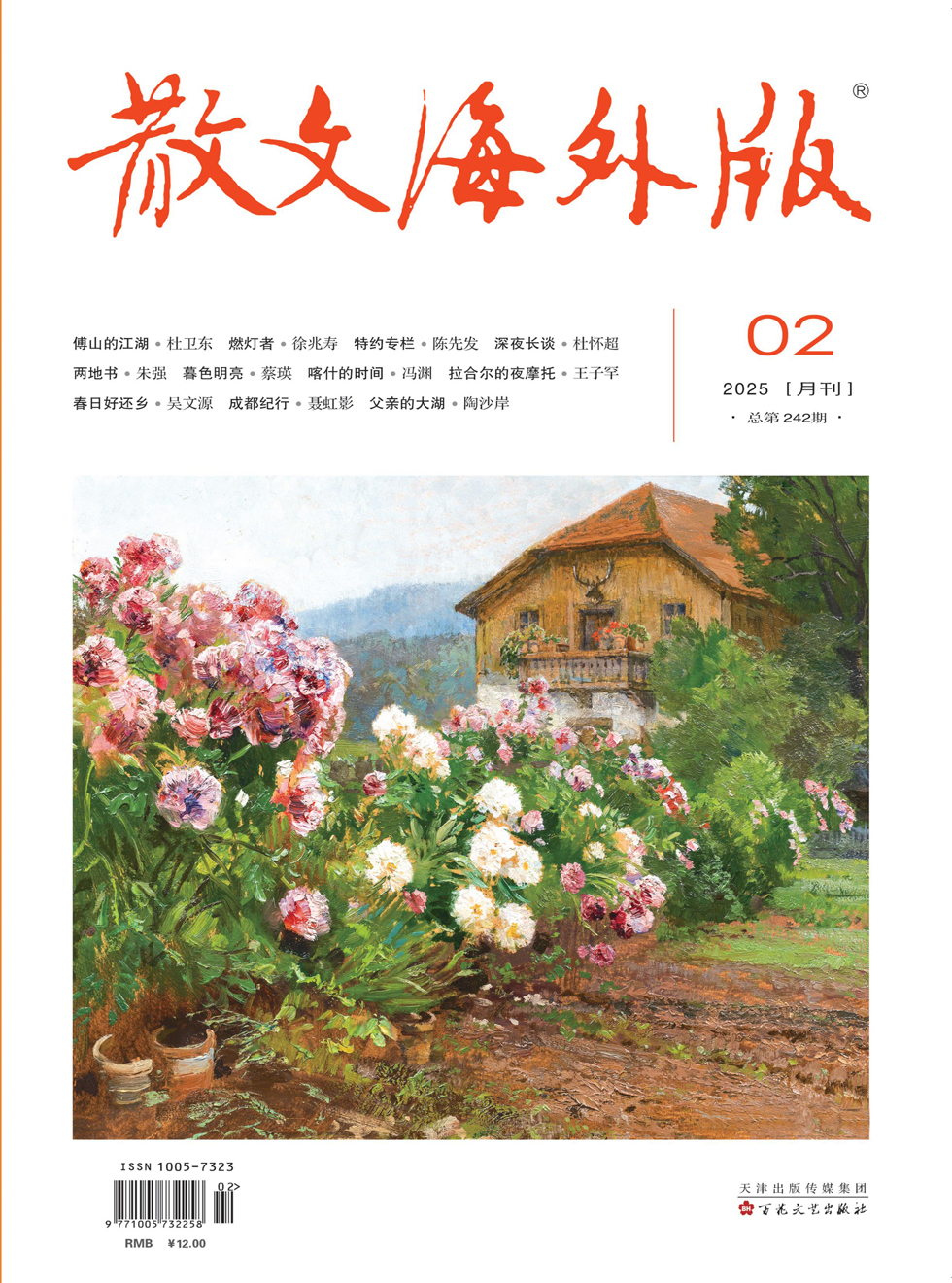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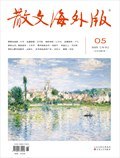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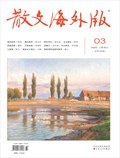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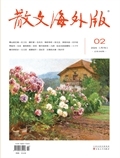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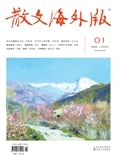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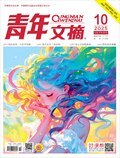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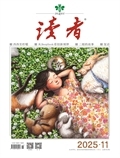

 登录
登录